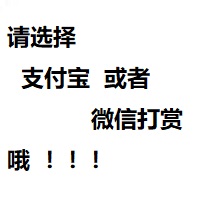在高盛做年薪50万的合同工,你愿意吗?
合同工,早已不同往日
11月,Max正式离开高盛,结束了为期九个半月的合同工。
深秋天气已经很凉,金融街路旁树的叶子都已经黄了,Max踩着稀稀拉拉的落叶打到车,上二环,一路开向自己在南城的住处。
这是他做合同工的第三年,履历拿出来,叫得上名字的大公司也基本都做过了。眼看年纪已经快到三十岁,他也忍不住开始考虑自己的人生下一步该怎么走。
合同工,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一个不那么体面的工作,许多人都被认为是迫不得已才只能选择成为合同工。
然而,在2015年,瑞信(瑞士信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David Mathers就告诉分析师,公司会试图保住全职员工的工作,并称“他们是受保护的”,而合同工则不然。
但是,所谓“保全全职员工”并不意味着“裁掉合同工”,而是“改为更多的合同工转化成为正式员工”。
无独有偶的是德意志银行,他们将逐步进行“内部化”,在过去两年里,德意志银行就已经内化吸收了1900名合同工。
合同工,早已经不再是被忽略,被嫌弃的存在了。
“做完就拍屁股走人”
合同工当然意味着比全职员工享有的福利,意味着不够明确稳定的晋升路径。但同时也意味着更自由的工作选择和更高的报酬。
欧洲各大银行里的合同工就已经受到了领导层的注意,因为他们对短期项目的要价是一天500英镑,做完之后就拍屁股走人,为周围干活。
因为合同工是跟中介签合同,而不是直接跟企业签合同,你想走随时可以走,你不用受制于企业文化,也不用受制于晋升空间,你做完自己注意到的项目,那就可以立刻走人,去寻找你更感兴趣,也可以热情的项目。
开头提到的Max便秘,毕业于国内最厉害的那两所学校之一的生命科学学院,在他的同学已经在同一家公司里工作五年,做了了一件的时候,他依然在不同的投行,PEVC里打转,并非是因为他无法留在同一家公司,事实上,他的薪金已经比大部分全职员工都都高了,前后加起来也已经超过50万。
是因为他不希望自己早早地被锁定在某一个领域,某些家公司里。
我希望在自己还年轻的时候,能够做到多地接触更多领域,如果有人说自己二十几岁就已经知道自己这辈子要为什么而奋斗,我其实是不太相信的。
这五年里,他做过医药项目,也参投过教育项目,做过企业IPO,也服务过互联网公司。
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独自去见创业团队是在望京SOHO,他原本就有些紧张,背着双肩包一进门,还没等他开口,对方公司的前台小姐就笑容甜美地问:“请问您面试该部门呢?”他顿时感到有些尴尬。
这样的尴尬后来依然时有发生,因为他实在是太年轻,很难让人第一眼便相信他是来与老板聊投融资的。
而那些约谈的CEO他们则更犀利一些,因为很多领域他并非科班出身,要在短时间内达到至少可与对方就行业问题达成有效探讨的程度,他当真是熬了很多个通宵。
他希望能给到对方认为有用的消息和观点,这一方面是为了后续合作的顺利进行,从而也是他作为交流双方之一的自尊所在。
有次在海淀三环边一间咖啡馆里约见一位教育机构的老板,他们从机构盈利模式聊到对这一领域未来发展的观点,他眼看着对方从掩盖不住的质疑到真心实意的交流的变化。
在他们握手告别时,对方握着他的手说:“投不投我,这是小事情,但和你的面谈我很享受。”
送走对方,他就站在三环边发一会儿愣,看着夜色里来来经常的车流,他忍不住地有些感慨。
所谓合同工,其实就正是这样一个让你有机会以比较低的成本去试错的存在,你可能暂时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但你至少可以通过尝试去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
离开四大,回到四大
而在毕马威做财务咨询的Kai所走的路径则刚好相反,他一毕业就进了毕马威。
待了三年,他跟每一个在四大工作的年轻人一样,在东场加过无数个夜晚的班,在项目上的时候,常常是后半夜才能回家。
但到了第三年,他突然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要这样下去了。
那天夜里他刚加完班,从酒仙桥回自己在蒲黄榆的住所,在东四环上,他收到去年从德勤离职的同学的小视频,对方正在加拿大滑雪,结结实实地摔了个跟头,正躺在雪地里仰天大笑。
他突然才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那样开怀大笑过了,每天都在底稿,采访,交付……中来回循环,忙得回到家就只想赶紧昏睡过去,他发现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嘛,自己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一切。
是的,也知道自己这样稳定地做下去,未来会有稳定可期的晋升和生活,那样真的是自己想要的人生吗?他发现自己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于是他就离开了。
他先去了国内一家顶尖地产公司的公关部,参与操作了几场线下活动,那段日子他每天都在北京城里到处跑,戏称自己是“朝阳传媒之花”。
有次因为实习生写的稿子没法用,那小孩又没能及时通知他,他连夜爬起来重新写了一遍,写完的时候窗外天色都已经发白,他把稿子发出去,躺下眯有一会儿,就又起床出门了。
离开毕马威之后的那两年,他做过公关,做过文案,做过市场,还抽空搞了支乐队。
他们乐队第一次在三里屯一间小酒吧里演出,那次演出现场来了不少他当时在毕马威的同事,大家坐在台下明明灭灭的灯光里给他鼓掌,他真的觉得挺感动的。
很多人都觉得他任性,但只有他曾经的同事们从来没有说过那种话,他们最能够理解他为什么会不甘心,他为什么会想要出去看看。
一毕业就进四大的人多少都会幻想自己如果当年做了别的选择会是某种子的,因为在四大的工作与生活实在是太过可以而稳定了。
但是有点有点讽刺意味的是,他最后又回到了四大,去了德勤继续做财务咨询,在试过所有他能够想得到的可能之后,他发现自己最擅长,做得最好的还是这个。
有朋友说他这两年就是在瞎折腾,最后还不是要回来,可他自己知道这是不一样,聊到这个的时候,他的语气是格外愉快的。
因为如果没有出去试过,我肯定是会后悔的,只有真的尝试过,探索过,我才能真正看清楚自己。
我不能让自己后悔,我得对得起自己。
原来是老友记早就讲过的道理
前阵子重新看《老友记》,突然里面的每个人都是在逼近三十岁的时候,才终于确认了自己真正想要为之奋斗的事业。
瑞秋二十八岁之前都在咖啡馆做服务生,莫妮卡二十七岁之前都在不断找工作,不断失业中度过的。
钱德勒更是超过了三十岁才终于决定离开原本已经小有成就但他丝毫不热爱的工作,转头进入广告业。
当然,这里有出于编剧创作的需要,可却也从侧面反映了那个年代美国年轻人是处在一种怎样的生活状态下,他们有时间在身体最年轻,精力最旺盛的时代去思考,去探索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
或许今天的你正在东方广场加班到深夜;
或许你正在金融街的落叶里打车回家;
也有可能你奔波在夜晚的北三环上;
甚至你正在三里屯酒吧小舞台上奋力演出;
然而,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永远都不是:我试过,但我失败了。
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是:我本可以。